人生有愛真無悔,學術伉俪若金湯—訪化學學院湯卡羅教授(上)
湯卡羅教授青少年時期是一位非常勤奮努力、熱愛學習、博聞強記的好學生,工作以後是一位尊師愛生、樂于助人、成果卓著的好老師。常言道:自助者,天助之;愛人者,人愛之;嚴于律已者,多寬以待人。讓我們一起領略湯老師那曲折艱辛而又非常精彩的人生道路,一定會對我們的學習、工作、生活有所啟發。
湯卡羅,Kaluo Tang,beat365教授,女,1939年8月生于上海。1957年考入beat365化學系,1963年本科畢業後師從邢其毅院士讀研究生。1966年研究生畢業,1968年被分配到重慶西南制藥一廠工作,任技術員。1978年調回beat365從事科研與教學工作。曆任化學系(學院)講師、副教授、教授等職,曾任國際雜原子化學會(ICHAC) 顧問委員會成員,兼任第26屆beat365校工會兼職副主席,教代會執委會副主任委員等職。2002年8月退休。湯卡羅熱愛教育事業,她教書育人,尊敬師長,愛護學生,受到老師和學生的愛戴。
湯卡羅早年參加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的工作,取得很好的成績。調回北大後,主要從事金屬有機化合物和原子簇合物的合成和結構研究,為納米材料的合成開創了新的途徑。湯卡羅主持或直接參與的科研項目有1項獲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1項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2項獲教育部自然科學二等獎。在國内外學術刊物上發表學術論文80餘篇,在國際、國内學術會議上作報告和海報交流共27次。曾在美國、日本、意大利、韓國、英國、瑞士、澳大利亞、波蘭、俄羅斯、加拿大等10多個國家進行學術交流。
01 / 滬上傳奇:少女心事愛學習
湯卡羅1939年8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甯波,父親湯玉卿,母親孫永卿。湯家與孫家都是當地的名門望族,民國時期也都是風光一時的民族企業家,思想開明,重視教育,所以湯卡羅的父母都受到了良好的現代教育。不過母親讀高中時由于健康原因休學了,父親則畢業于位于南京的金陵大學,解放後為新中國建設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1931年湯卡羅父母的結婚照
湯卡羅是家中第三個孩子。大概是受男女平等及其它西化思潮的影響,父親給她取了一個以C開頭的意大利男性名字Carlo,意思是“可愛的”,音譯為卡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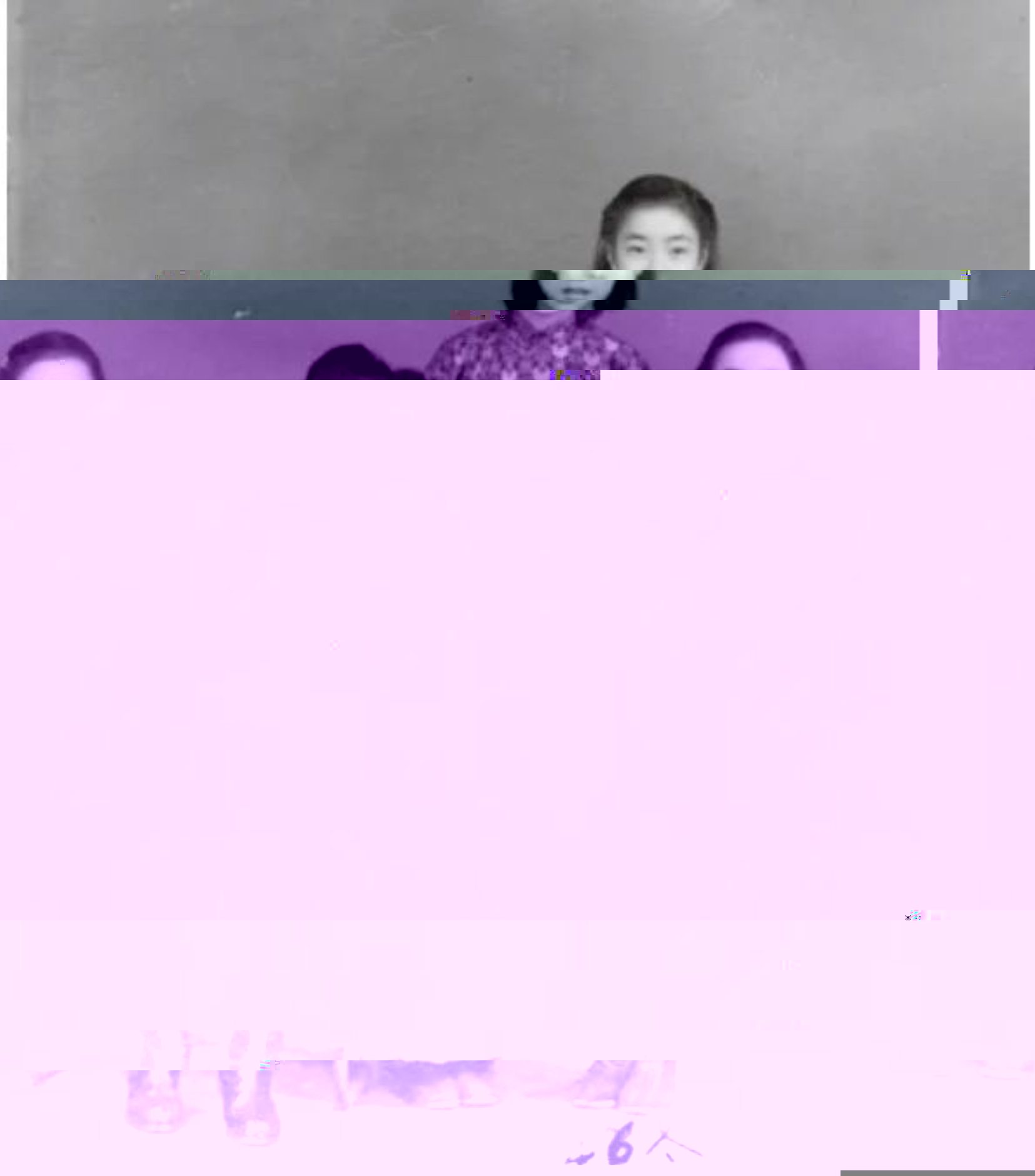
1946年湯卡羅(左)五姐弟與母親合影
湯卡羅自幼對學習、對知識是一種發自内心的喜愛,充滿熱情,樂在其中,是所有老師眼中的好學生,家長口中的好孩子,同學心中的好榜樣。湯卡羅對待學習不是那種立志報國或出人頭地的寒窗苦讀,學習對她來說不是負擔或任務,而是一種享受,也因此學習成為了湯卡羅老師貫穿一生的生活習慣。退休之後她還參加了電腦培訓班,為了學習拼音輸入法,花了二年時間把新華字典從頭至尾背了兩遍,補了解放前小學沒有漢語拼音的課。現在80多歲的湯老師能熟練使用各種常用的電腦軟件及手機APP。
“我小時候确實跟其他孩子有點不太一樣,他(她)們都更喜歡玩、做遊戲,而我則更喜歡學習。現在回想起來,以前的生活大部時候是很苦的,學習環境也很糟糕,但我隻要能學習就會覺得很開心。1946年我剛上小學一年級,我們家就搬到了上海虹口。先在一個公立閘北小學上了兩年,後來母親發現這個學校的教育質量很差,三年級時就把我轉學到家斜對面不遠的守真堂小學上學。這是一個美國人創辦的教會學校,學校管理非常嚴格,教學要求也很高,所有的課程都是70分及格。我們小學五年級就要學習10門文化課。不過我們那時課程分得比較細,比如英語就有口語、語法、習字三門,語文也有國語和古文文選兩門,其它課程是算術、曆史、地理、自然等,另外還有另交學費的鋼琴課。我從6歲開始學鋼琴,啟蒙老師是上海音樂學院王家恩教授,我們搬家後嫌路遠不去了,正好就在學校繼續學了。我非常喜歡這個學校,8點鐘上課,我不到6點就起來了,尤其冬天,早上6點天還是黑的。那時家裡沒有煤氣,保姆也要起來生煤爐子給我做飯,經常埋怨我。我匆匆忙忙吃幾口泡飯,自己歪七扭八地梳好辮子就去學校了。到學校大概6點半左右,看門的工友還沒起床,我就敲門。我那時個子小,自己從路邊撿一塊磚,站在磚上踮起腳才能按到門鈴。我記得那個工友叫做老王,揉揉眼睛就出來了,很不高興地問我為什麼這麼早來。”
“特别是冬天,我坐在空無一人、燈光昏暗的教室裡,外面又黑乎乎一片,後來想起來其實有點後怕。教室有三個門,黑闆兩旁和教室後面各有一個門。上海的冬天刮起風來,門被吹得哐哐地響,而且非常冷。不過我當時完全沒有害怕的感覺,就是坐在那裡複習功課,把所學的課本全部默寫出來。這個學校類似貴族學校,學費很貴,但前三名有獎勵,第一名學費全免,第二名免一半,第三名免三分之一。從四年級起,我的考試成績一直是第一名,不過我另外一位同學有不知什麼名目的加分,所以我是第二名。每學期結束,拿個大紅包獎學金回家,給家裡免一半的學費,我也很開心。”

守真堂1916年建成,2000年重新翻修。守真堂小學在其南側和後面。(攝于2006年)
“在守真堂小學給我打下了很好的學習基礎。學校課程多、要求嚴格,但不是死記硬背,老師會講解原理和有趣的故事。比如我們數學用的是一本叫《劉編算術》的教材,裡面的題目很難,也有很有趣,比如著名的‘雞免同籠’、‘植樹問題’等我們在四年級就學了。我能把這些複雜的算式道理搞明白,并給同學們講解,這培養了我的獨立思考和理解能力”。
“1949年4月中旬,我正上四年級時,由于戰事吃緊,我們停課。不上學了,小孩子們都很高興。那時候因為害怕停水,家家戶戶都用水缸儲備了很多水,鄰居的孩子都拿水槍打水玩,唯獨我抱了個書包,愁眉苦臉地坐在一邊。我母親回憶說從來沒見過為不能上學而發愁的小學生。”

1949年湯卡羅小學四年級
“上海在5月20日解放,再過了一個月我們就開課了。守真堂小學因為是教會辦的學校,我們周六放假,周日上午到旁邊的教堂去做禮拜,唱贊美詩,聽聖經故事。解放後也沒變。到第二年,報紙上就點名批評我們學校了。我媽覺得情況不對,就把我和妹妹轉到了北站區的第二中心小學,我在那裡上六年級,妹妹上四年級。相比而言,這邊的課程就很容易了,基本上老師一出題,我就知道答案了,因為大部分内容我早就學過了。然後我就很順利地考上了上海中學。那時上中的入學考試是相當難的,錄取比例是25:1。上中在上海郊區,學生都要求住宿,媽媽就說‘正好你那麼喜歡到學校去,幹脆住校吧!’于是,剛滿12歲,我就在離家30多裡的上海中學住校了。”
“上海中學目前已有150多年的曆史,可以說一直是全國最好的中學之一,其教育理念、課程設置、教學方法、師資力量都符合人才培養的要求。學校的創建者有很長遠的發展眼光,校園占地面積相當大,我記得那時有400畝地,建在離上海市中心很遠的郊區。住校學生周一到周六不允許随意出來,有特殊情況需要向班主任請假,并要教導處批準。我們早上6點起床,10分鐘後要到操場鍛煉,然後上早自習,吃早飯,上課。學生每人都必須參加兩個課外興趣小組,一個是文藝方面的,另一個文化課方面的。我們下午4:30下課,然後是學習方面的興趣小組,我選的是化學;5:30是藝術方面興趣組,我選的是鋼琴。我從初二開始還給學生合唱團鋼琴伴奏。我們合唱團參加上海市中學生文藝彙演還得了一等獎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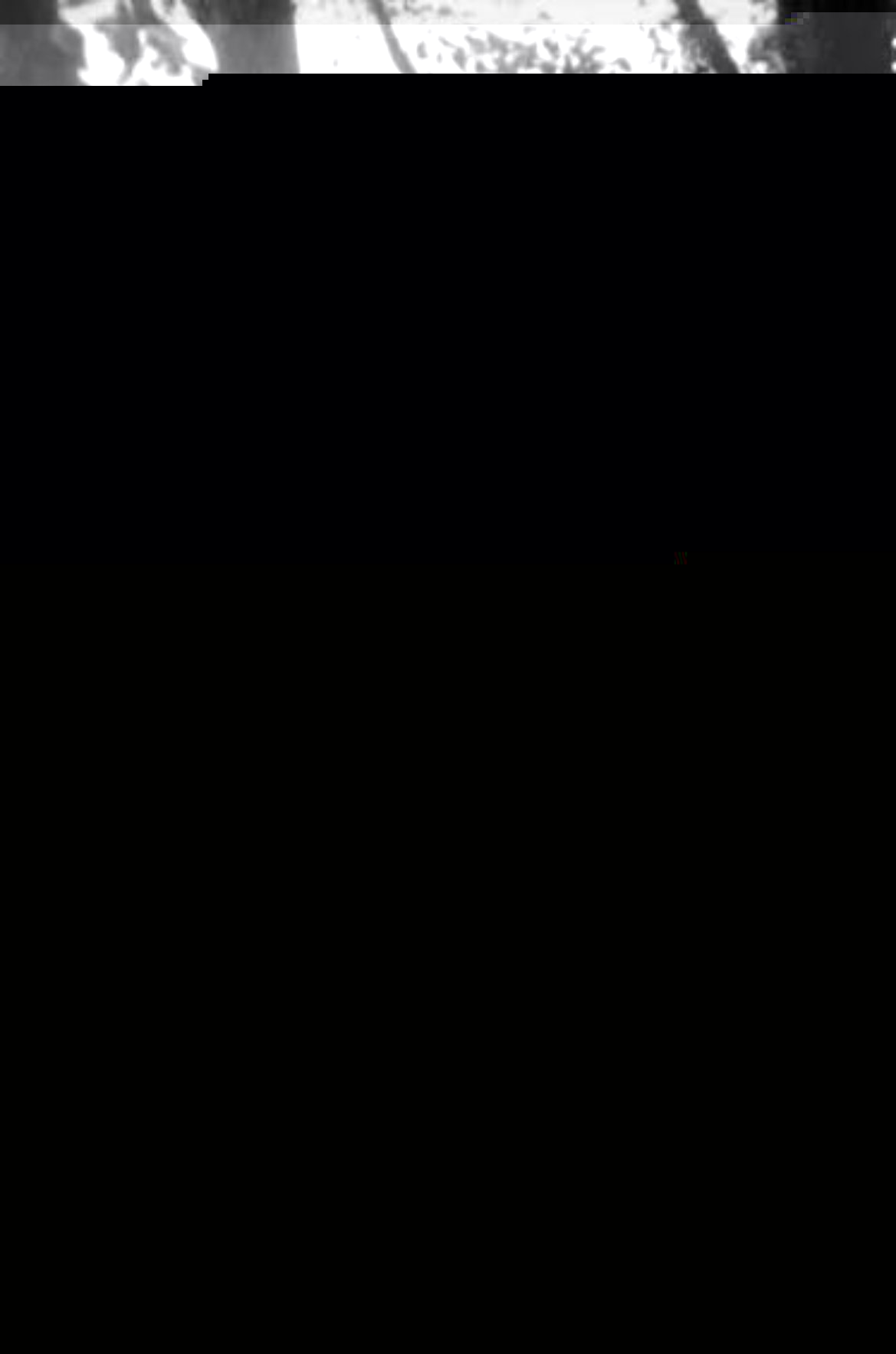
1957年湯卡羅高中畢業 (攝于上中校園)
“學校很重視興趣小組,給予相當高的經費支持,化學組每人每年25元。要知道那時的一年學費初中才12元,高中16元。我從初二開始上化學課,就特别喜歡化學,覺得化學特别有趣,還容易學。初二第一學期,我化學課所有的大小考試和平時測驗都是100分,化學老師也特别喜歡我。于是,我就參加了化學小組,沒想到它後來成了我畢生的事業。初中時,是老師提供實驗資料,我們照着做就是了。從高中開始就要求自己設計一個實驗,先寫一個報告,寫明實驗目的,需要的儀器和試劑,實驗内容、過程,以及如何進行等。由老師陪同,獨立操作。在初中時我們制作了肥皂、牙膏等産品,到高中還做了合成橡膠、酚醛樹脂等。這為我以後的學習,打了很好的基礎。”
“我從初中開始上課時有記筆記的習慣。記得我初二時有一次曆史小測驗,考了68分,我非常傷心。有人向班主任報告了,說我哭了,因為覺得對不起爸爸媽媽。老師批評了我,說我學習目的不正确,要為國家建設而學習。後來我在曆史課上非常用心,上課時記筆記,努力記住要點。曆史老師并不知道,有一次上課時,他看我從開始一直在寫東西,就要我站起來,問我在寫什麼?我說正在記筆記,你的話我已經全部記錄下來了。他不信,然後我念給他聽,老師聽到後臉都紅了。之後我做任何事情都喜歡記錄,上課和開會都有記錄,從小養成了‘好記性不如爛筆頭’的習慣。後來我跟下一代的孩子們也這樣講,記筆記使人精力集中,尤其高水平的老師,講課時有很多解讀和即興發揮,記筆記對學習會很有幫助。”

1993年10月重返母校(龍門樓前)
“1954年我初中畢業,獲得免試直升高中的獎勵。那時是以10%的比例選取的,每個班也隻有5人。老師教育我們還要學做社會工作,我當了班級文娛委員,後來又在學生會當了幹事。1955年,上海開始實行表彰‘三好學生’(身體好、學習好、工作好)。我是上海中學第一批‘三好學生’,連續三年,直至高中畢業。我之前的體育成績一直不佳,100米要跑22秒。于是每天早起鍛煉,練習跑步和跳高、跳遠等,總算通過了‘勞衛制’的要求。到高中畢業時我所有科目的成績都是優秀。”

1993年10月拜訪恩師唐秀穎(左,上海中學數學特級教師)
“上海中學的教育理念是培養德智體美全面發展的學生。學校也鼓勵我們以北大、清華為目标,每年會張榜公布錄取北大、清華的‘光榮榜’。不過功夫在平時,不是那種高強度的題海訓練。高考前兩個月我們就放假了,回家自己複習。那時上海考到北大、清華的學生特别多,教育部開始限制這兩所學校在上海的招生總數。盡管如此,我記得很清楚,那年北大共招收上海生源108人,整好一節車廂。北大派一位老師來上海組織,所有的學生沒有家長陪同,學生半價票是9元9角,我們的火車晚上9:00開車,經過兩天三夜60個小時,第四天早上9:00到達北京前門火車站。我們坐的是學生加班車,超級慢,每個小站都停。那時從上海到北京的普通旅客快車需要27小時,特快24小時。因為多數同學都是第一次出遠門,開始時都很興奮,到了第二、三天受不了,就橫七豎八地躺在地闆或行李架上。”
02/ 那時燕園:同學少年,峥嵘歲月
“前門火車站有北大的校車接我們,車開出來就到了天安門。在北大剛開始我們住12齋,現在老化學樓和電教樓中間位置的二層小樓,早已經拆掉了。我們的宿舍是一個大房間,中間用木闆隔成三間,每間6個上下鋪,住12個人。大概半年左右, 學生宿舍35齋蓋好了,我們就搬了過去。”
湯卡羅從小就是一個非常自覺自律的人,做事情非常有條理、有計劃,不像有的學生需要老師和家長的全程督促,這也使她到了大學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學習習慣和學習熱情。“我從小喜歡讀書,認為學習是一種享受。北大校園比較大,不同的課、做實驗的地方往往相距很遠,那時也沒有自行車,我都是一路小跑,因為我喜歡搶到第一排正中間的位置。我們那時隻有星期日休息,一般人可能想難得睡個懶覺,而我周日早上5:00就起床了,去圖書館搶位子。6點多門開了,我差不多第一個沖進去,找好位置放下書包,除了吃飯,一整天都在圖書館學習。平常如果沒有學校安排的活動我幾乎不出校門,我到大學五年級才第一次去了故宮。”
“一進大學我就當了北大學生文工團鋼琴隊的隊長。因為原來在上海中學的老同學認識我,他們推薦的。1958年中央音樂學院開辦了業餘部,二年制專科,面向社會,主要是到各大學招生。北大學生會推薦并資助我去學鋼琴,一個星期去上一次課,一個學期學費16元。教師是招翠馨老師一對一上課,課外要用5比1的時間練習。每學期要考試(鋼琴由周廣仁、朱工一教授主持考試),然後把成績單發給北大學生會,不合格就退學。我努力學習鋼琴,得到老師好評,順利地拿到了畢業證書。當然我在北大的化學課也沒有耽誤,按現在的說法我算是獲得了雙學位。這期間我加倍努力,總覺得時間不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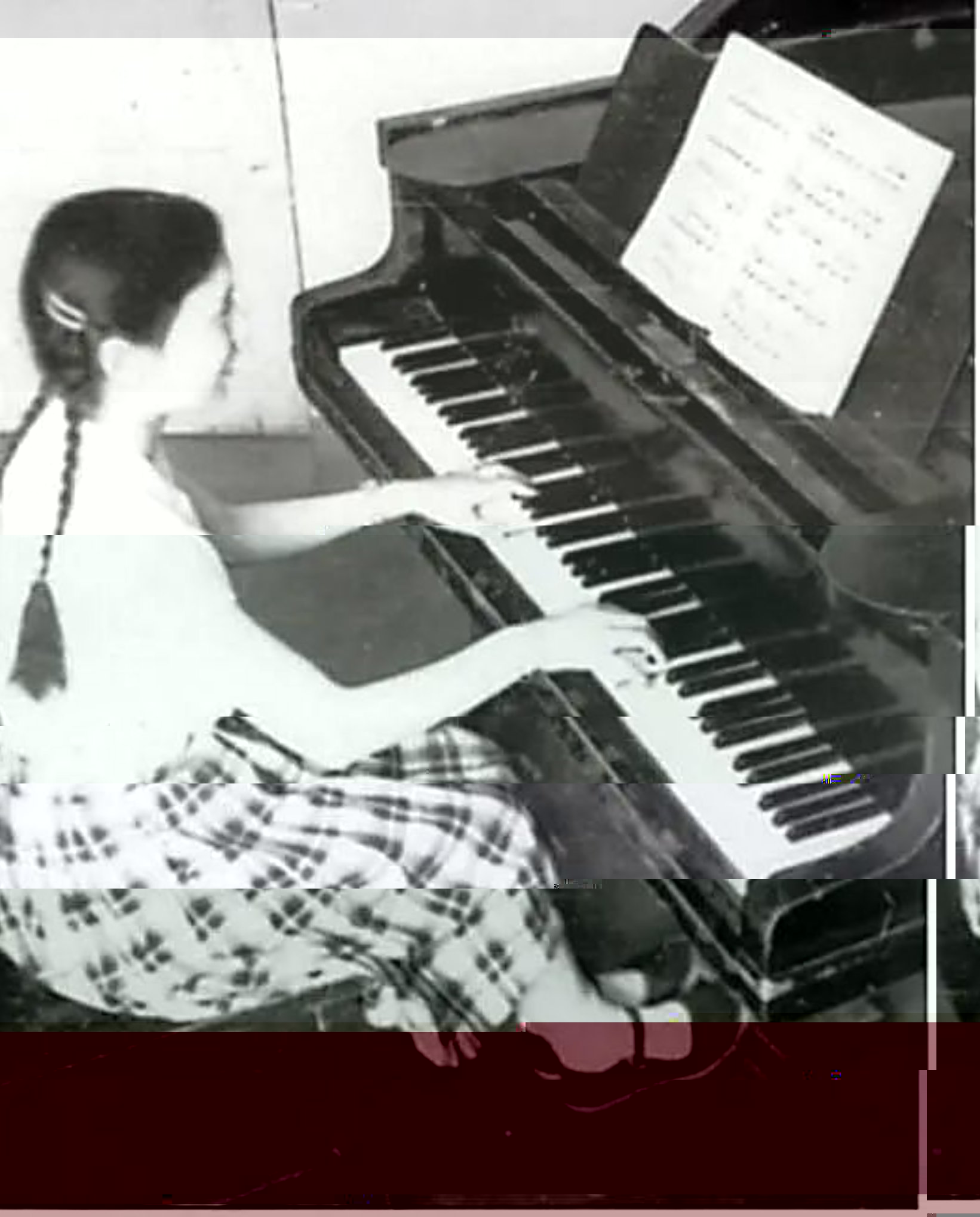
1960年在北大鋼琴房練琴
“1960年之後又是三年困難時期,那時食堂夥食真是非常差,真是餓着肚子念書。主食是發黴的陳玉米面和白薯面做的小窩頭,每頓隻有兩個。菜就兩樣:白菜幫子或茄子。現在燕南美食的地方,以前有個菜窖。我們不上課時,就去幫忙倒白菜,每天工作一個小時。給白菜通風透氣,防止腐爛,把白菜從一個牆根搬到另一個牆根,順便把最外面的菜幫子掰下來送到食堂做菜。那時菜幫子也是很珍貴的,我們一人隻有一小勺。我對那段時間的茄子印象非常深刻,到現在我也不吃茄子。白水煮茄子,加一點鹽,我吃到嘴裡就覺得一陣陣反胃,所以有茄子的時候我就隻要窩頭。食堂打飯的師傅覺得奇怪,他就問我怎麼回事,我說吃了會吐。那位師傅很好心,讓我把一周的菜票交給他,他給我打一碗辣醬。我就這樣一碗辣醬當菜吃一周,同學們還羨慕得不得了。那時很多人浮腫,腿上一摁一個坑。很多同學餓得沒力氣,就躺在宿舍裡‘勞逸結合’。然而我還是努力學習,圖書館不開門,我就在鋼琴室學習。自學英語,一個詞一個詞地查字典,硬是把一本費塞爾編著的英文原版的《有機化學》啃下來了。”
那幾年湯卡羅家裡也非常困難,父親被打成右派,工資減了一大半,母親沒工作,弟弟妹妹也在上學,食宿、交通及學雜費成了大問題。母親為了維持一家的生計,把解放後幸存的家底,比如自己的狐皮大衣、貂皮圍脖,父親的西裝,家裡的鋼琴、收音機、照相機、望遠鏡、派克金筆等都變賣一空。但還是不夠,以至1960年暑假湯卡羅回家後,母親含淚勸她退學。幸虧有一位親戚(母親的内侄孫年增)仗義資助。他說“卡羅這樣從小喜歡讀書、又讀得好的孩子不讓上學,天理不容呀!以後她的生活費由我負擔。” 此後他每兩個月資助25元,湯卡羅才得以繼續上學。1963年畢業,從小愛學習的她想考研究生,媽媽說“你小學、中學、大學,上了18年,不要再上了。上研究生收入也少,家裡又有負擔,生活會很苦的。”但是不怕吃苦的湯卡羅,堅持要考。上了研究生後,還從每月42元的微薄助學金中分出16元寄給在複旦讀大學的弟弟湯毅堅交夥食費,全家才得以渡過難關。
“我們那年考研究生特别難。1962年招生制度改革,研究生由過去的‘保送’改為自由報名、嚴格考試、擇優錄取,招生原則是‘甯缺毋濫’,名額特别少。規定隻有教授才有招生資格,而且每個教授一年隻能招收1至3名研究生,每位教授指導的在讀研究生總數不得超過5名。北大化學系雖然是全國知名教授最多的,1963年也隻錄取了8名研究生,整個北大理科也不過20多人。這些教授招收研究生不但看考試成績,還要通過親自指導他們做本科畢業論文進行全面考察,才決定是否錄取。這樣一來,外校的學生基本沒有機會。不過事有湊巧,那一年北大化學系破例錄取了複旦大學化學系的應屆畢業生金祥林。這是因為在物理化學考試中,有一道題漏寫了解題的條件,使該題變得無解。金祥林不但指出了該題無解,而且自己修改考題,加上條件,把題目做出來了,這讓唐有祺教授大為贊賞。金祥林原本報的是中科院化學所,因為唐教授也在那邊任職,而那邊的招生名額已經滿了,就把他招到了北大化學系。”
“研究生我是跟着邢其毅先生讀的,本科畢業論文就是邢先生指導的。那時候基本每天晚上都做實驗到深夜,整個老化學樓隻剩下我一個人。等我離開的時候,樓道的燈都關了,大門也鎖了,我摸黑一路開燈,從三樓走下來敲傳達室的門。我還記得那位工友外号叫‘荷蘭鬼’,因為以前有一部著名的恐怖電影叫《飛翔的荷蘭人》,他的眼睛跟劇中人物有點像。因為我經常叫他開門,影響他休息,‘荷蘭鬼’很不高興,罵我的語氣跟我小學時給我開門的工友很像,不過不同的是,小時候我請求放我進去,現在是請求放我出去。哈哈!”
“我們讀研究生時除了英語和政治,不上其他課。專業學習通過寫專題報告的方式,給你一個課題,讓你查閱資料,你自己總結發揮。我記得高等有機化學‘考試’,我交了100頁稿紙,寫了一個暑假。當時規定研究生考試隻要有一門課不及格,不準補考,退學另行分配工作。當時我們化學系硬是有2位研究生被退了,所以我壓力特别大。”
北大化學系的邢其毅先生德高望重,對待教學與科研工作都非常嚴謹。從1964年3月開始,北大化學系派陸德培、李崇熙、施溥濤、季愛雪和葉蘊華到中科院上海有機所進行牛胰島素人工合成的科研攻關,邢先生是北大攻關組的負責人。當年暑假施溥濤老師因為教學工作需要返回北大,邢先生就把正在讀研究生的湯卡羅派過去加入這一課題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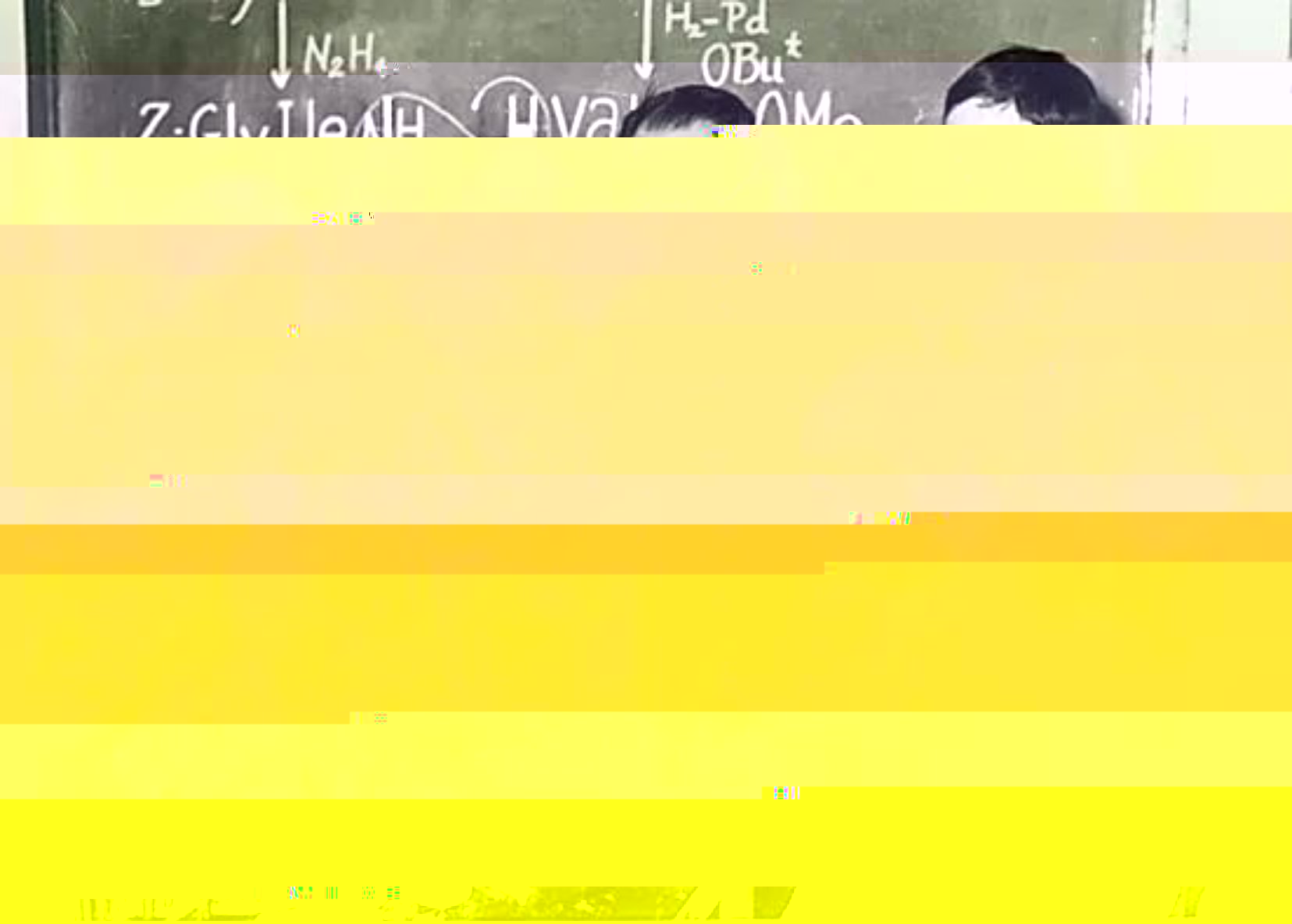
胰島素組在北大10齋做實驗(左起湯卡羅、邢先生、李崇熙,坐着的是季愛雪、葉蘊華)
“合成牛胰島素是中國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有世界影響力的科研成果。這個項目是‘大躍進’時候提出的,後來因為群衆運動搞科研‘大兵團作戰’而徒勞無功。李崇熙老師和陸德培老師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對項目的最終完成功不可沒。群衆運動之後,李老師和季老師留下來收拾殘局。一瓶瓶的原料和中間産物,顔色都差不多,為了保密,很多标簽還是别人看不懂的編号。幾位老師對藥品及遺留下來的資料進行了盡可能的梳理,并繼續進行一些與胰島素相關的多肽合成方面的研究。”
“人工合成蛋白質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課題,而作為最簡單的蛋白質,國外一直有人在從事胰島素合成方面的研究。到1963年底,美國的卡佐亞尼斯(P.G.Katsoyannis)在美國化學會會刊發表了一篇簡報,聲稱得到了微弱活性的人工羊胰島素。國内得知這個消息時的情景我記得非常清楚:李崇熙非常激動,拿着那個雜志就跳到了我們的實驗台上。他在實驗台上向我們發表演說:如果我們不抓緊,等于前功盡棄,這麼多年來的人力和物力都是白費。我們必須趕超他的微弱活性,全合成為純胰島素結晶!大家受到他的感染,也都非常激動。”
“這個項目因為受到國家科委主任聶榮臻的支持而重新啟動,并确定了由中科院上海生化所、有機所與北大化學系合作攻關的方案。上海那邊不願意來北京,邢其毅先生表示我們可以派人過去。上海那邊又說沒有你們的肥皂票和肉票,你們來了,生活會有很多困難。大家又表示肥皂我們可以背過去,肉我們可以不吃,态度非常堅決。到上海有機所後,雙方合作比較愉快,項目進展總體也很順利。施溥濤因工作原因回來後,上海有機所的汪猷先生說人手不能減少,邢先生就把我派過去了。”
“那時之前,我已準備開始撰寫我的研究生論文了,是另外一個課題。資料已經查好,藥品也開始準備。邢先生對我說應該服從大局需求,我當然沒有什麼可以說的。邢先生又對我說,在上海我要有獨立的工作與創新之處作為我研究生畢業論文,然後為我制定了一條與大家不同的合成方案。”
湯卡羅的工作是獨立完成胰島素A鍊氨端九肽的合成,用疊氮法,而北大科研組原來用的是碳二亞胺法。結果兩個方法合成的化合物性質完全相同。湯卡羅驗證了其他人的工作及邢先生提出的新方案的可行性,而且得到了更高的得率(碳二亞胺法得率42%,疊氮法得率為60%)。中國科研人員世界首次全人工合成結晶牛胰島素是生物化學領域一個裡程碑式的事件,其過程的曲折艱辛,相關科技工作者的智慧與辛苦無疑值得大書特書。不過鑒于此事親曆者的回憶文章和文獻資料已相當完備,在此就不再贅述。湯卡羅依據參與這一工作的科研成果撰寫了高水平的研究生畢業論文。由于科研及撰寫文獻綜述的需要,還要查閱大量的英文及德文文獻,對中學及大學都是以俄文為第一外語的她來說,自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湯卡羅當年的畢業論文、撰寫的文獻綜述、工作報告,以及上海科教電影制片廠後來拍攝的采訪視頻,現在都在北大化學學院作為珍貴資料保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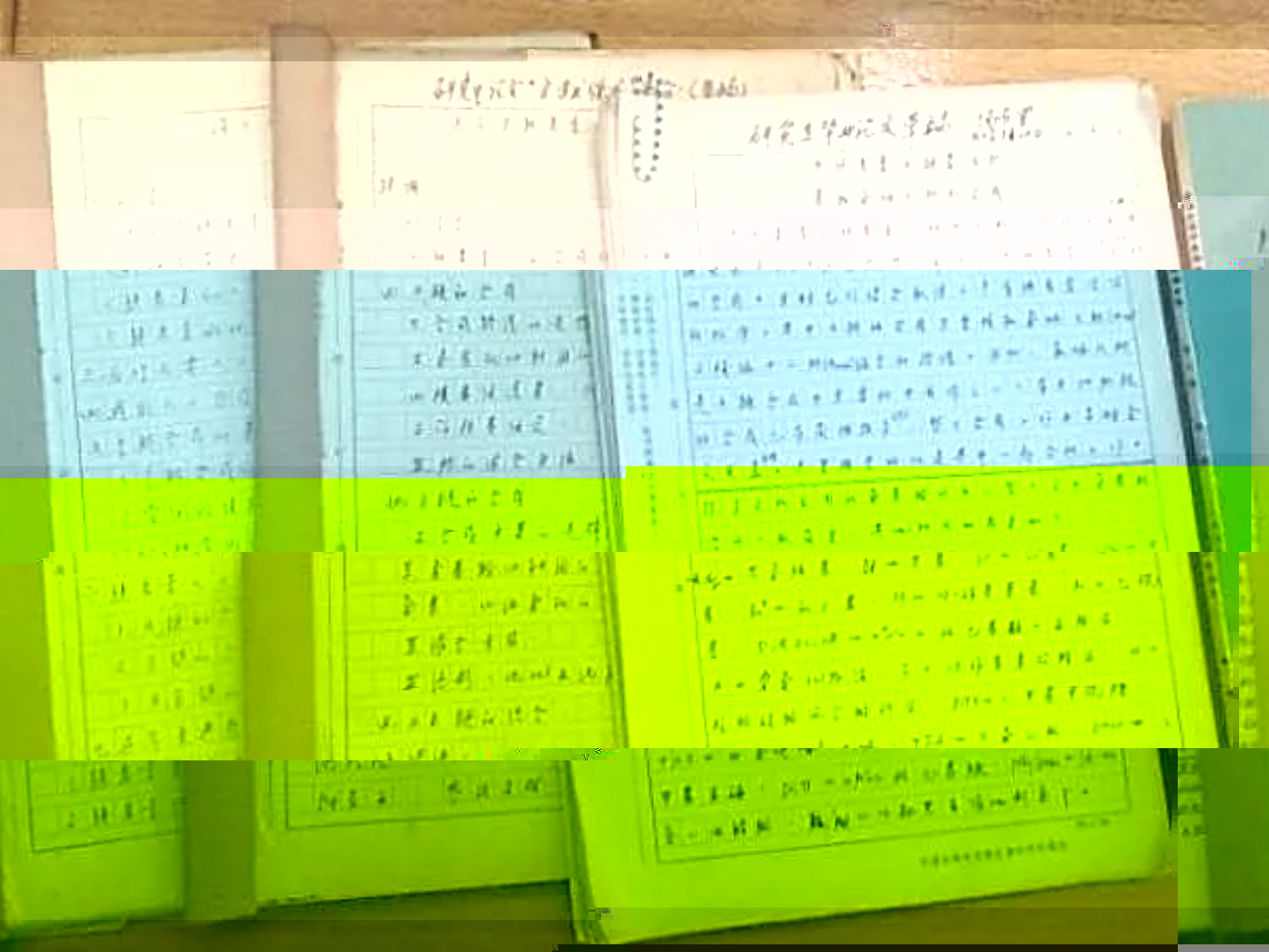
湯卡羅研究生畢業論文草稿、文獻綜述等手稿
“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成果于1982年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并發放1萬元獎金,由3個單位的四個科研小組分,北大分到2500元。學校、系裡、教研室都會留一部分,我記得最後分給了我200元。我拿到這筆錢後,逛畫展時看到一幅有兩頭小牛的風景油畫覺得很喜歡,就花30元買了下來,一直挂在卧室裡。”

胰島素合成獲得國家自然科學一等獎後所購買的紀念油畫
湯卡羅1966暑假研究生畢業,然而不幸的是,當年5月份 “文化大革命”爆發了,正常的教學、科研、招生及畢業生分配工作都停止了。1967年5月1日,在動蕩的社會環境中患難與共的湯卡羅與金祥林舉辦了簡單而溫馨的婚禮,這對珠聯璧合的新人從此相互扶持、相互依靠、伉俪情深,共同經曆了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在beat365留下了一段“固若金湯”的佳話。

1967年在頤和園拍的結婚照
“我們在北大進行了兩年文革,然後1968年重新分配,研究生全部掃地出門,學校一個不留,說我們是‘修正主義苗子’。不過科學院的研究生倒是受到優待,可以留北京工作。我被分到重慶的西南制藥一廠。金祥林是做結構化學的,文革前唐有祺先生設想的方案是讓金老師留校,在國家重點實驗室工作。1968年重新分配時,學校一度把金祥林給忘了,後來給他補了一個方案,把他分到成都的抗菌素研究所。這樣我們倆人同在四川還分兩地。研究所的條件可能會比工廠要好一點,但他們不要倆人。金老師就說,‘兩個人還是在一起好,我作犧牲,跟湯卡羅去工廠’。就這樣,我們倆最後都被分到了重慶的西南制藥一廠。那時候邢先生、唐先生他們都被關在牛棚裡,我們動身前都未能向他們告别。”
03/ 火爐曆練:金子到哪裡都會發光
“我們1968年8月16日到達重慶。那時從北京到重慶火車要50多個小時,我們坐硬座兩天兩夜,下車時我的腳都坐腫了。我們的工廠位于重慶大學下面的山坡上,山坡的下面即嘉陵江。當看到所謂‘西南制藥一廠’隻是十幾間破房子和破棚子的時候,想到自己以後就要這裡工作和生活,我心都涼了。報到時廠裡的書記還不願意要我們,說是沒地方住。我們對他說,不是我們要來的,你可以把我們退回去。于是他給上級醫藥公司打電話,結果上級讓他必須接收,因為這是國家任務。我們先是住在隻用大半截牆隔成房間的招待所裡,上面是通的,隔壁房間有動靜都聽得到,夜裡巨大的四川耗子(注:那時重慶還不是直轄市,歸四川省管轄,所以耗子還是四川‘戶口’)就在牆上肆無忌憚地跑來跑去,真不知是哪位建築師的‘天才’設計。半年後我們才住進一間十幾平米沒有廚房和廁所的格子間裡。”
文革時期重慶地區武鬥非常嚴重,對立派别甚至使用軍用制式武器火拼。每日槍炮聲不斷,再加上艱苦的生活條件和簡陋的工作環境,湯卡羅與金祥林的心情可想而知。那時的“西南制藥一廠”其實更像一個手工作坊,日常工作更多的是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二位不但工作上任勞任怨,而且充分發揮自身的專業素養與創造力,取得了一項了不起的技術革新成果:“痢特靈技術革新一條龍”。
“‘痢特靈’是一種治療痢疾、腸胃炎等病症的小分子藥,學名叫5-硝基呋喃唑酮,化學式為C8H7N3O5,是西南制藥一廠的主要産品之一。原來的生産工藝要使用光氣做中間産物。光氣是一種劇毒的氣體,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曾用作化學武器,造成大量傷亡。廠裡為了‘改造’知識分子,特地将金老師安排到制備光氣的車間幹活,之前已經有很多工人中毒病倒了。制備光氣要使用一氧化碳和氯氣,當時正好沒有一氧化碳了,因此工人們在閑聊,按四川話講叫‘擺龍門陣’。金老師進來,有工人就對他說:‘你不是北大來的研究生嗎?你能不能幫我們想想辦法,把生産路線改一改,不用光氣行不行?’”
“金老師是學結構化學的,有機合成并不是他的專業,但他有機化學的知識也很紮實,就整天琢磨這個問題怎麼解決。有一天半夜我已經睡着了,金老師把我推醒,說他想到一個可能的合成路線,可以避開光氣,問我可不可行。我是搞有機合成的,覺得他的方案理論上沒問題,就說天亮了到工廠圖書室去查一下資料。”
“西南制藥一廠雖然不起眼,但圖書室的資料非常齊全。這得感謝廠裡原來的一位老工程師叫鄭壽,他是解放前中央研究院一位著名的研究員。剛解放時,比較重視知識分子,他經軍管會同意,到香港把需要的化學文摘(CA)、美國化學會志(JACS)等外文資料,從1907年開始都買齊帶回來了。文革開始後說他當年去香港是從事特務活動的,被打倒,每天掃廁所。他見人不說話,我們也不敢和他交流。”
“我查閱資料發現國際上有人做過類似反應,金老師提出的方案雖然有所不同,但應該也是可行的,于是我們就着手做實驗。那時車間裡沒有實驗室,我們就把必要的設備放在一個乒乓球台上。實驗需要電動攪拌器,也沒有,我們就用馬達和自行車飛輪改裝了一個簡易的。這個實驗需要4步反應,每一步的中間産物都要正确無誤,但廠裡沒有分析儀器和分析手段,我們隻能憑經驗和觀察。我們心情非常激動,顧不上休息,連續工作了36個小時,直到最後黃色的痢特靈産生。那時我們簡直要跳起來,比當年成功合成胰島素還高興。”
“新工藝正式投産要到1969年底或1970年初了,用的是全新的生産路線。從小型試驗、擴大中試直至正式投産,金祥林夜以繼日連續高強度工作六個多月,以至于患肺炎、發高燒。不久金祥林當上了痢特靈車間的主管技術員,他繼續搞革新,修改多處生産工藝,生産成本不斷降低。之後他又研究中間體的處理、廢氣的回收等等,又涉及好多步反應,又花了好多年。他一步一步做了大量的工作,使痢特靈的售價從每片6角降低到2分錢。所以這個項目叫‘痢特靈技術革新一條龍’,1979年獲四川省發明二等獎,得了兩千元獎金。獎金全廠都發了,而我們因工作調動一分錢都沒得。金老師也沒争,覺得為國家做了貢獻就夠了。”
“金老師是特别厚道、樂于助人的人。按規定,主管技術員是不需要參加三班倒的,但他經常剛下日班,準備吃晚飯時,組長就來說某某有病上不了夜班,他二話沒說就去頂夜班了。重慶是有名的‘火爐’,每年夏天至少有一兩個月時間最高溫度在39℃以上,金祥林還要在五六十度的反應鍋旁操作,他幾乎年年都要中暑、發高燒。”
“這個新工藝很快在全國推廣,無償使用。全國各個準備生産痢特靈的制藥廠都來學習,金老師耐心講解,手把手操作。别的廠學得都還比較順利,但江蘇省鹽城制藥廠三次來人都沒有學會。金老師就說:‘我去鹽城教你們。’他一個人去的鹽城,回來跟我講經過,有些事情特别逗。他說,鹽城那個廠非常簡陋,工人們技術也差,很多事情都不會做。比如大型離心機裡面要襯個尼龍布口袋,那個離心機口袋他們就不會做。金老師會踩縫紉機,連離心機用的口袋都幫他們做了。鹽城制藥廠後來也成功生産起痢特靈了,那裡的人幾乎都知道金老師,說是四川重慶來了一個技術員啥都會幹。金老師就是這麼一個人,特别的無私,争着幹活,卻從沒想要什麼報酬,從中獲取什麼利益。金老師這個人一直都是踏踏實實做事,不為名不為利,我們回到北大後也是這樣。譬如,他在X射線衍射儀組工作,剛開始是十個人,三四個人一班,三班倒。到後來,人越來越少,有的人調到别的組去了,還有兩個人去世了,最後隻剩他一個人管這台儀器。組裡有對外服務,人家拿樣品來測試,北大要收測試費。測一個晶體結構1000元,一部分上交學校,一部分交系裡和教研室,剩下的組裡提成,十個人時分成十份,後來就金老師一個人做了,還是在組裡分。他就是這麼一個人,寬以待人,從不跟人計較。”
痢特靈在20世紀末幾乎是老幼皆知的“神藥”。那時國家經濟不發達,人民生活窮困,許多人營養不良,飯菜一點都不敢浪費,發馊發臭的往往也要吃掉。而且絕大多數家庭又沒有冰箱,食物很容易變質,衛生條件和衛生意識也差,普遍講究“不幹不淨,吃了沒病”,所以急性腸胃炎導緻的“跑肚拉稀”是常有的事。身體差的,不及時就醫,往往要持續數天,從而造成嚴重脫水,甚至危及生命。如果服用幾片痢特靈,基本就是藥到病除。金祥林老師雖不是痢特靈的發明者,但他改進的生産工藝,保證了藥廠的安全生産,創造了可觀的經濟效益。而且将痢特靈價格由6角降到2分錢一片,讓人人都吃得起,更是為提高全國人民健康水平做出了無法估量的貢獻。(那時6角錢價值好幾斤大米,吃不飽飯的普通群衆真舍不得買。)
“這種藥物的分子非常穩定,可以存放幾十年都不變質。我離開時重慶帶過來的痢特靈現在還可以吃,有時候拉肚子,隻要吃1-2片就足夠了。”
湯卡羅進廠時分配在度米芬車間勞動,接受再教育。度米芬是一種消毒用的季铵鹽。湯卡羅在成品工段,每天要和工人一起把幾十斤重的原料擡到操作台上投料,要用木榔頭把結塊的成品敲碎,成品放在真空幹燥器裡,要用扳手把24個卡鉗上緊......勞動強度對她來說是相當大的,以至于1969年3月她才懷孕3個月就流産了。金祥林心疼她,背了背簍走了20多裡山路,到農村買回了一隻老母雞和一些雞蛋,給她補補身體。湯卡羅休息了兩個星期後,還是要在車間裡接着幹活,所以金祥林就想辦法抽空去幫幫她,減輕一點勞累。後來廠裡接到研究戰備止血藥的任務,1970年1月把湯卡羅調到制藥廠的研究室工作,任止血藥組組長。組裡一共12個人:除湯卡羅之外,有3個文革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和1個中專生,2個老工人,3個複員軍人,2個知青。日常工作除了做化學合成研究外,還要上山采藥,到農村買狗做實驗.....主要用化學合成藥物和中草藥篩選有止血功能的藥物。幾年時間裡,湯卡羅帶領同事合成了幾十種化合物和中草藥提取物,并自己做動物實驗,發現幾個像鞣花酸等有止血功能的藥物。這期間,湯卡羅還曾被調到二車間搞左旋咪唑的拆分和提純研究,獲得成功并投入生産。此外,湯卡羅研究小組還為藥用聚乙二醇6000的提純做了大量工作,并獲得成功,為西南制藥三廠生産提供了有利的生産條件。湯卡羅于1970年3月再次懷孕,在年底生下了女兒金晶。由于藥廠的生活和工作條件使得湯卡羅沒法自己帶嬰兒,金晶就留在上海外婆家,直至三歲多到了重慶,一家三口才得以團圓。
西南制藥一廠雖然廠房破敗,但重視圖書資料的傳統卻一直保留了下來。除了舊有的專業雜志,廠裡還每年撥款3000元訂閱購買國内外的最新期刊,這事也由湯老師負責,這也為湯老師的一些研究工作,以及後來輔導廠裡的大學生及知識青年學習提供了便利。
文革期間“抓革命,促生産”,工廠生産也不斷受到政治運動的幹擾,時常停工。另外由于文革開始後全國學校都停課了,之後大學在校生直接分配,中學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廠裡又陸續分配來大約60多位沒讀完大學的大學生,以及一些初中高中階段的青年工人。雖然那時盛行“讀書無用論”,大家也不知道文革還要持續多久,但湯老師還是對這些青年荒廢時間感到憂心,于是就給組裡的年輕人補習功課,主要是化學和英語,後來擴展到全廠。在湯老師的悉心教育和督促之下,這些年輕人勤奮學習,文革結束後有好幾個大學生考上了研究生。

1975年一家三口在重慶
文革結束後,經過中央“撥亂反正”,大學恢複招生,向科學進軍的口号重新被提出,科學的春天來到了!這使文革時期遭到“流放”的知識分子看到了在更合适的崗位上為國家建設出力的希望。
“1978年3月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梁棟材先生被作為落實知識分子政策的典型,從湛江調回北京。我們受到鼓舞,就給北大化學系唐有祺先生、邢其毅先生寫信,希望調回北大。唐先生、邢先生也樂意讓我們回來,還征得了北大有關領導的同意。然而工廠卻不願意放我們走。我們隻好給國務院主管科教的方毅副總理寫了一封信。信封上很簡單,就是‘國務院 方毅副總理收’。方毅副總理很快就對此信作了批複,并派人來廠裡核實,他要求四川省委盡快對此做處理。當時四川省委副書記冀朝鑄寫了八個字的批示:‘人才難得,應予調整’。他還指示重慶市委和化工局的領導要限時解決我們的問題。”
“沒想到重慶市化工局沒有和北京方面聯系,就給我們發了調令。離開重慶要到8個部門蓋章,其間還有很多波折,差點兒沒走成。尤其進京戶口,是唐有祺先生親自出馬,和北大黨委書記周林一起到北京市委幫我們辦的。在他們的幫助下,北京市委給我們一家三口特批了三個進京戶口。在唐先生百歲誕辰時,我們倆再次向唐先生道謝,真是師恩難忘啊!”

2020年唐有祺院士百歲壽辰時,湯卡羅夫婦向唐先生道謝“師恩難忘!”
記者 | 郭九苓、高珍、劉宇
錄音整理、文字編輯 | 郭九苓
排版 | 祝晨旭
審核 | 湯卡羅、高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