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同行 學術友緣—訪化學學院李宣文教授(上)
李宣文老師出生于1933年,他的整個學生時代及教學科研生涯反映了國家的苦難、動蕩以及發展。而處變不驚、自強自立、以誠待人的人生态度,以及“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知識分子風骨——這是李老師送給後輩們最寶貴的财富。
李宣文,Xuanwen Li,beat365beat365教授,男,1933年生,山東省壽光縣人。1953年考入beat365化學系,1957年畢業後留校從事催化專業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任催化教研室副主任與主任(1960~1997年),1998年退休。1992年獲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1966年3月至1967年7月作為中法建交後國家派出的第一批科技進修生,在法國裡昂催化研究所從事分子篩催化劑的研究。
李宣文參加十餘項國家科委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重大項目、重點項目、國際合作項目和橫向合作項目的研究,發表學術論文百餘篇,獲發明專利9項。曾任中國化學會催化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化工學會第35屆理事、中國顆粒學會第一屆理事及顆粒測試委員會副主任,中國科學院蘭州化學物理研究所羰基合成與選擇氧化國家重點實驗室學術委員、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中法催化聯合實驗室學術委員、中國石油大學重質油國家重點實驗室客座教授等職。
01 /自強自立的學生時代
李宣文老師1933年生于山東壽光縣侯鎮一個普通的農村貧寒家庭,家中除了父母,還有一個哥哥和三個妹妹。解放前的北方農村,一般家庭的生活都是極其貧困的,缺衣少食、饑寒交迫是常有的事情。李宣文的父親是個比較有遠見的農民,再困難也要讓兄弟兩人讀書。李宣文與哥哥學習很用功,念完小學後,因為1946年壽光縣沒有中學,父親就送他們到40公裡外的濰縣(現在的濰坊市)讀中學。1945年壽光已經解放了,而濰縣還沒解放,上學途中要經過國民黨警衛人員的盤問與搜查,經曆千辛萬苦,他們才能從解放區到達“敵占區”的濰縣。當時的濰縣中學沒有學生宿舍,他們的父親就托朋友把兄弟倆安排到濰縣一所有學生宿舍的廣文中學(教會中學)讀書。教會學校要交學費,當時通貨膨脹非常嚴重,錢不值錢,糧食就成了最重要的資源,所以學校收糧食作為學費。李宣文兄弟倆每個月都要徒步從學校到家裡往返,帶上自己的口糧以及鹹菜維持基本的生活。由于吃飯沒有油水和蔬菜,兄弟倆都患了夜盲症,真所謂是“寒窗苦讀”。李宣文的父母更加不容易,兩個男孩不能幫忙下地幹活,還要帶走家裡寶貴的糧食。
“我上初中是1946年,到1947年濰縣解放,濰縣一中也有宿舍了,而且不收學費,因為我和哥哥成績都比較好,所以在1949年初三的時候就轉到濰縣一中。濰縣一中在當地是很有名的,數學、物理、化學等方面師資力量都很強,如鞏憲文、李蓬先、鄭心亭等老師,所以是很多學子們向往和追求的名校。老師們豐富的教學經驗和循循善誘的教學方法,不僅使我們學習到必要的基礎科學知識,而且啟發了我們對科學的熱愛和對理想的追求。其中鄭心亭老師對神秘的化學變化及其規律所做的深入淺出的講解和饒有趣味的描述,使我對化學産生了濃厚的興趣,立志要學習化學。”
李宣文兄弟二人都非常懂事,也很聰明,中學畢業都考上了名牌大學。“父親希望我們中學畢業後,至少能回壽光當個小學老師,不用再過‘面朝黃土背朝天’的生活他就很滿足了。解放後各方面急需人才進行建設,國家鼓勵上大學,上大學不但不收學費,還免費吃住,所以我們就決定考大學了。”
1953年李宣文順利地考入beat365化學系,他哥哥李宣德考上上海第一醫學院(後來是毛主席和周總理醫療小組成員之一)。他們哥倆幫助家裡收割了豆子等農作物,打掃了場院後才離家各自上大學。
建國後高校普遍擴大招生規模,但基礎設施、硬件條件還沒跟上。“我們入校以後沒有新生宿舍,男生在第一體育館打地鋪,女生住在第二體育館,不過青年學生滿懷報國熱情,這些絲毫沒有影響大家的學習熱情。記得在1953年beat365新生開學典禮上,學校教務長嚴仁庚發表了激動人心的歡迎詞。他說‘歡迎你們在新中國開始進入大規模經濟建設時期進入beat365。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實施了,156項重大建設工程項目将為國家的工業化奠定基礎。改變國家貧窮落後的面貌,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曆史使命就落在你們青年一代的身上’。國家的雄偉發展規劃,鼓舞人心的歡迎詞使我們認識到上大學的責任,我們下定決心要為國家的發展和建設而努力學習。”
李宣文本來就是一個喜歡學習、善于學習的勤奮學生,在上級組織的激勵和良好校風的鼓舞下更加努力上進,德智體全面發展取得很大的進步,于1955年被評為beat3651954-1955年度優秀生,并獲得校長馬寅初頒發的beat365優秀生獎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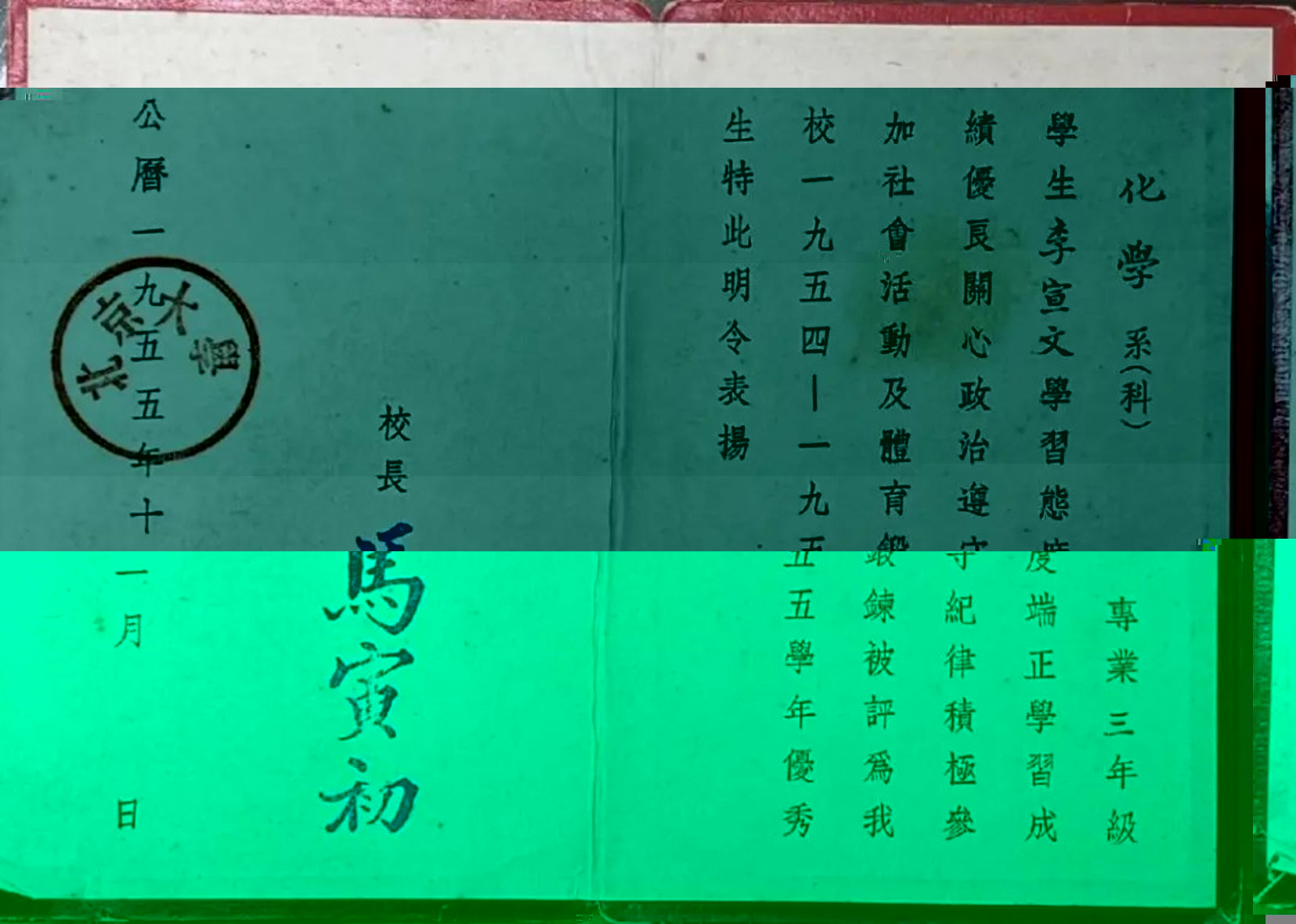
馬寅初頒發的beat365優秀生獎狀
“第一年我不太适應大學的課程學習,内容和要求都與中學差異很大。那時全盤蘇化,采用蘇聯教材,考試為口試,分數改為5分制。第一年我的學習成績都是三分,剛及格。第二年我加倍努力,與學習好的同學交流對我幫助非常大。有的同學學習方法好,同學之間的交流使我們相互之間取長補短,我經常有茅塞頓開、事半功倍的感覺。我們經常一起到實驗室,一起到圖書館,有問題随時互相讨論共同提高。另外我也經常請教老師,不懂就問,老師給予我許多啟發和建議,所以我學習方面提高比較快,與同學、老師關系也相處得比較好。到了1955年三年級時,我的學習成績就全優了。除了刻苦學習,我還積極參加上級号召的各種社會活動和體育鍛煉,并于1955年5月加入了中國共産黨。”
時代雖然不斷在變,但李宣文老師的學習經驗對當前的大學生仍有重要的參考意義。北大有許多非常優秀的學生和老師,互相交流往往能夠互相啟發。不管是提問還是回答,亦或平等的辯論,雙方都需要理清思路、組織語言,不隻是知識的學習,對思維與表達能力都是很好的訓練。
02/參與創建國内第一個有機催化教研室
1957年李宣文大學畢業留校後,被分配到有機高分子教研室工作。因為使用适當的催化劑和催化工藝,可以大大降低某些化學反應的條件要求,提高化學反應速度與反應産率,抑制副産物的發生等等,可以說催化是現代化學工業的靈魂。由于國家建設急需發展化學工業,為更好地培養催化方面的專業人才,學校決定在化學系建立有機催化教研室,由龐禮教授領導,李琬、張嘉郁、張山樵和李宣文參加。
“當時一切從零開始,沒有教材和教學計劃,參考資料非常少。我們到圖書館查閱有限的資料,并多方請教懂行的專家,從中梳理有關催化方面的知識。沒有實驗室,沒有儀器設備,在缺乏科研經費的條件下,我們在張嘉郁老師的帶領下,因陋就簡,就地取材,自己摸索制造了反應爐與控溫設備,并且研制、改造了多種分析儀器。”
“建立催化專業也得到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1958年北大邀請蘇聯專家德魯斯(Д.B.Друзъ)為我們講授催化課程。在兩年期間,協助我們為55級催化專業的學生開設了‘有機催化’和‘催化理論’兩門課程,并指導青年教師開展用電位法研究液相催化加氫催化劑與催化反應。”

1958年在蘇聯專家德魯斯指導下進行科學研究
有了催化教材,又有了教學所需的實驗設備,才具備成立教研室的條件。1960年學校決定在北大正式成立全國第一個有機催化教研室,任命龐禮教授為教研室主任,李宣文為教研室副主任。1985年龐禮教授退休後李宣文接任主任,直到1997年。
“1960年,中國科學院邀請蘇聯專家基别爾曼(C.L.Киперман)到中科院化學研究所講學,他是蘇聯科學院捷林斯基有機化學研究所的多相催化動力學專家。催化教研室的同事們感到多相催化動力學是我們教學與科研中的薄弱環節,紛紛到化學研究所聽課。大家認真聽講,主動提問,有時還涉及課程之外的多相催化動力學研究問題,這引起了基别爾曼的注意。當他了解到這些主要聽衆來自beat365化學系,而且特别希望學習并開展多相催化動力學研究後,就主動提出上午在化學研究所講課,下午到beat365化學系工作,幫助建立循環流動法研究多相催化動力學的實驗裝置,并指導進行科學研究。因此他就成為非我校邀請的、卻在我校工作的蘇聯專家。在半年的教學與科研中,他在我們多相催化動力學的教學與科研方面給予了大力的支持,并與我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1960年上半年,正是中蘇激烈論戰的時期。我們在學習批判蘇修的‘九評’文章,他回蘇聯大使館要學習批判中國的文件,可我們雙方都心照不宣,他仍盡心盡力地做着他份外的工作。他在回國前曾私下對我說:‘我們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是任何力量破壞不了的!’盡管如此,中蘇關系的破裂使得雙方不能繼續進行學術交流。直到1990年,已是蘇聯通訊院士的他和布拉金教授有機會再次訪問中國時,不幸受到某單位外事部門工作人員的冷遇。後來他與我聯系上,我便請他們到beat365做學術報告,并邀請他們到我家做客,還陪同他們到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參觀訪問。兩位專家在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外事處的安排下遊覽了長城和定陵,愉快地結束了中國之行。基别爾曼在最後告别時說:‘我們之間還是好朋友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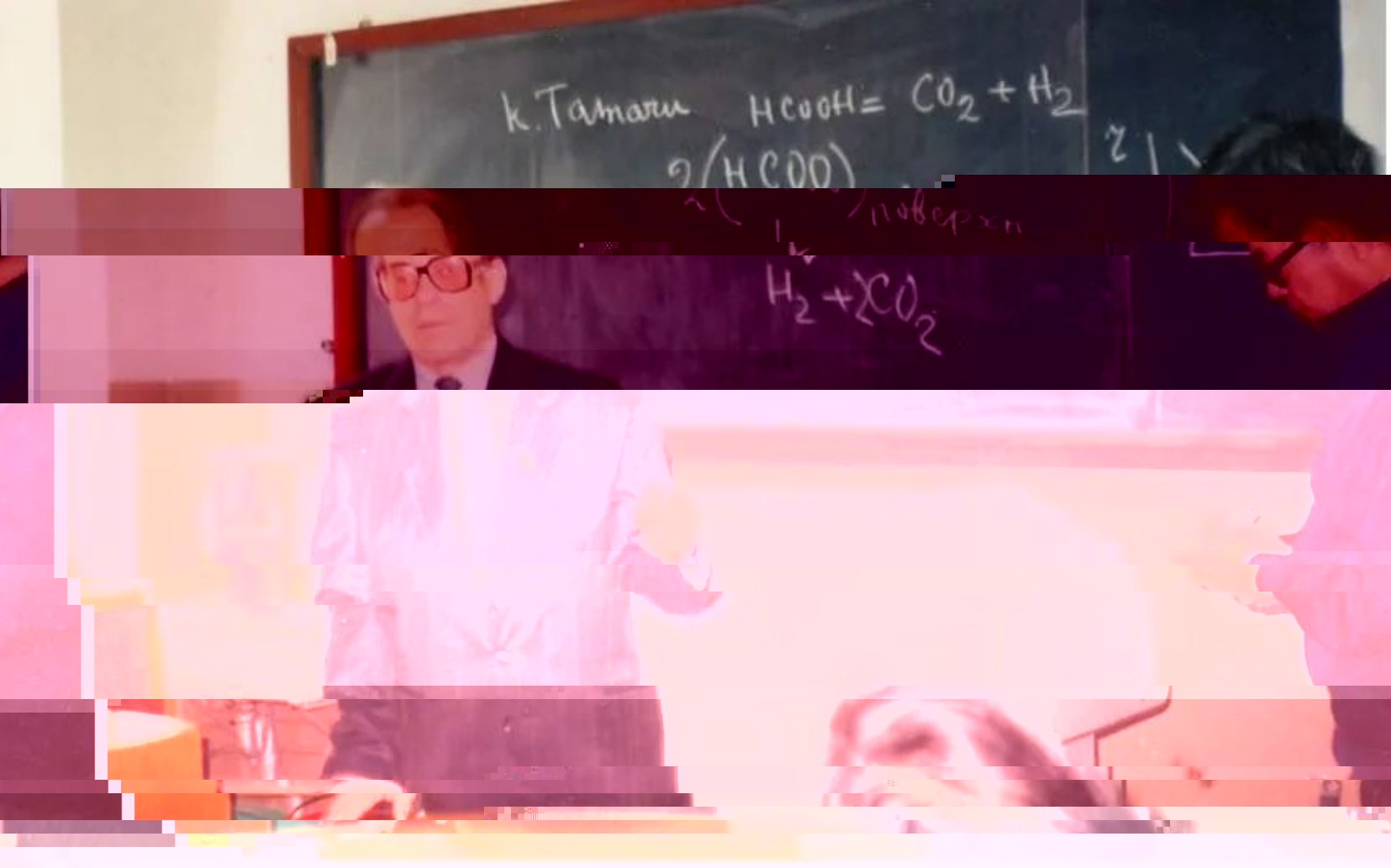
1990年基别爾曼在北大做學術報告(黃志淵翻譯)
“1961年,為加強催化教研室的建設,系領導決定将孫承谔、李作駿、丁餘慶與研究生何淡雲等四人從物化教研室調到催化教研室,與從蘇聯留學回國的俞啟全一起進行多相催化動力學方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至此催化教研室已初具規模,科學研究、課程建設、人才培養基本走上正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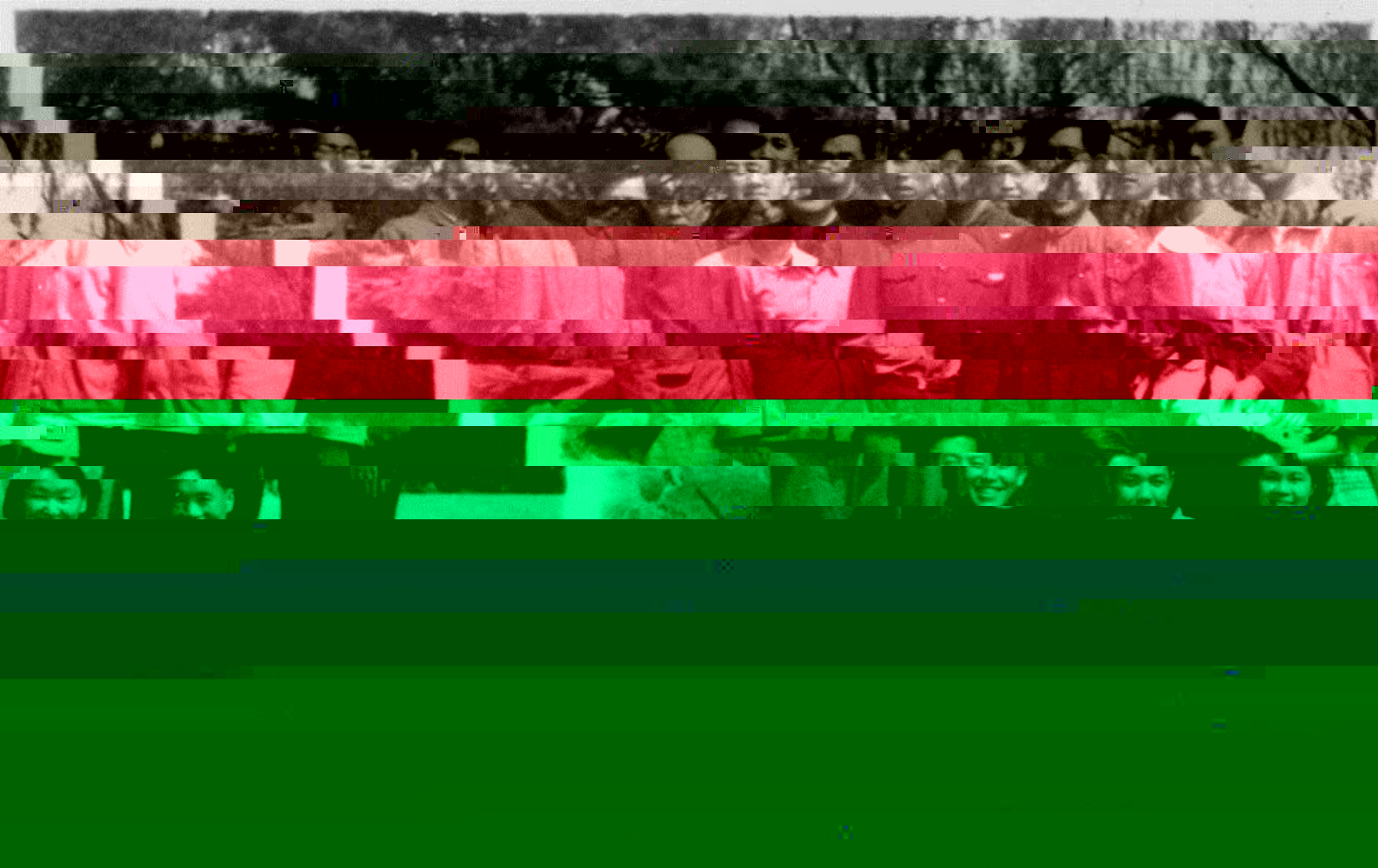
1961年催化教研室的教師與研究生的合影
(坐在前排的從左至右為龐禮、張嘉郁、佘勵勤、李琬、吳克瑞、後排站立者從左至右為楊錫堯、王秀山、俞啟全、孫承谔、楊永年、李作駿、高正中、李宣文、丁餘慶)
“1962年初,我們把蘇聯專家德魯斯于1958-1960年為催化專業學生講的‘有機催化’和‘催化理論’兩門課程認真整理,并打印成正式的教材,後來一直被作為催化專業的主要參考書籍使用。在此期間,張嘉郁、佘勵勤、楊錫堯、楊永年和我還編寫了1962-1963年使用的《有機催化實驗》教材,1964年又增加了實驗内容,編寫了新的《有機催化實驗》(一)、(二)。第一部分内容是實驗裝置的制作和實驗方法,第二部分内容是有機催化反應實驗。催化實驗教材是我們因陋就簡建成實驗室後,在實踐中不斷積累和總結經驗編寫出來的。教材中注重培養學生獨立思考和動手的能力,如管式爐的設計與催化動力學的研究等。實驗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有很大幫助。除上述教材外,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我還為工農兵學員編寫了《催化劑及催化作用基礎知識》。雖然這些教材因當時條件所限隻能油印,但在多年的教學過程中,為培養催化專業人才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以上教材現存放在大連化學物理所建立的“中國催化史料館”中
有機催化教研室建立後,從1959年開始正式培養出第一屆55級催化專業的學生20餘名,以後每年都有20餘名本科生分配到催化專業學習。下面是1963年第三屆57級(六年制本科生)催化專業學生畢業照。

文革結束後,教學工作恢複正常,教研室同事們團結合作,開設了“有機催化”、“催化作用原理”、“多相催化反應動力學”、“化學文獻”、“氣相色譜在催化研究中的應用”、“化工原理”以及“催化專門化實驗”等課程。催化教研室成立近40年培養了許多大學本科生、研究生和進修教師,為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工業部門輸送了一批專業人才。他們中間大多數畢業生成為教學與科研中的骨幹與學術帶頭人,其中四名畢業生和一位進修教師在他們從事的專業工作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分别成為科學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李老師為本科生和研究生講授了“多相催化作用原理”、“分子篩的結構、性能與工業應用”、“煉油工業反應中的酸式催化與碳正離子反應機理”、“紅外光譜在化學吸附和催化劑酸性測定中的應用”等課程。後來李老師應邀在中石化石油化工科學研究院研究生部及中國石油大學講授催化課程,并協助指導研究生的科研工作等,另外還在中國科學院科技大學研究生班(北京)等高校講授催化課程,可謂桃李遍天下。
在采訪中,現已90歲高齡的李老師深情地說:“我永遠不會忘記老催化同事們的團結合作精神,以及為培養催化專業人才所做的貢獻。非常感謝老同事們對我工作的一貫支持。”

2006年催化教研室退休老師聚會後合影前排左起:佘勵勤,黃秀珍,裴占芬,張慧心,任韶玲,金韻
後排左起:劉興雲,俞啟全,李國英,楊永年,李宣文,張嘉郁,楊錫堯
03 /“文革”前到法國進修
新中國成立後曾長期不被西方國家承認。1964年1月,法國戴高樂總統第一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法建交,同時與中國政府簽署了有關科技教育的合作協議。中國教育部決定向法國公派留學生,李宣文老師有幸被選中。
“當年11月,我正在湖北荊州搞‘四清’時接到教育部通知,要我去上海外語學院留學預備部學習法語。大學期間學習俄語,現在轉學法語,要從學習字母開始,老師要求我們每天要熟背50個單詞及有關句子。經過一年多的法語強化培訓,1966年初,我和另外六名法語班同學首先被法國政府接受赴法留學,成為中法建交後中國派往法國的第一批科技進修生。七人進修的專業分别為數學(中科院數學所張關泉)、生物化學(南開大學李建民)、催化化學(beat365李宣文)、微生物學(中科院微生物所莊增輝)、遺傳學(中科院遺傳所司穉東)、地質學(北京地質學院郭步英)和土木工程(上海同濟大學蔡國鈞)。由于中法之間沒有直航,我們先乘五天四夜的火車到莫斯科,然後從莫斯科飛往巴黎。法國是一個世界聞名的國家,在哲學、文學、藝術、科學技術甚至生活方式等方面對世界有廣泛的影響,是文人志士、藝術家和科技人員所向往的地方。我能去法國進修感到既興奮又緊張,不知能否适應西方國家的生活與工作。”
“法國外交部給我們每人提供了三年的獎學金,每人每月700法郎。當時國家外彙緊張,我們每月交300法郎給大使館,餘下的400法郎用于日常的食宿。上世紀60年代,中國還處于封閉狀态,法國是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到法國後,有許多嚴格的規定,如外出時要三人同行等。我們留法七人中有六人在巴黎,隻有我一人在裡昂。當時使館領導比較開明,告訴我,既然一人去裡昂工作,要注意安全,遇事要‘堅持原則,禮尚往來’。這樣,我一個人來往于巴黎和裡昂之間,活動的自由度比較大,大家都非常羨慕。我每兩周回巴黎大使館一次,彙報工作和參加政治學習。時任中國駐法大使黃鎮非常關心我們七人的工作和生活,回使館時,他常給我們介紹國内外的形勢,還專門讓廚師為我們開小竈。”

1966年初在巴黎聖母院前
左起:莊增輝,李宣文,郭步英,蔡國鈞,張關泉,李建民,司穉東
“1966年3月我進入裡昂催化研究所,所長Marcel Prettre先生征求我的意見後,将我安排到C.Naccache博士的實驗室,進行分子篩催化劑的研究。Y型分子篩是1959年美國 Mobil公司首先開發出來的固體催化劑材料,是具有規則孔道結構的結晶矽鋁酸鹽,它有很大的比表面和酸性中心數目以及良好的孔道傳輸性能,制成催化裂化催化劑後能産生巨大的經濟效益。據統計,1963年僅北美地區的煉油廠,就因為使用了Y型分子篩裂化催化劑取代傳統的矽酸鋁催化劑,一年純經濟收益達 53億美元。Y型分子篩催化劑的優異催化性能和産生巨大經濟效益的潛力,吸引着世界各國科學家競相研究。當時,Y型分子篩催化劑的精細結構、酸性中心如何産生及其在Y型分子篩結構中的位置都還沒有弄清楚,這是國際上熱門研究的課題。”
“研究分子篩催化劑,需要測定分子篩催化劑的比表面、孔體積、結晶度和晶粒大小。制成催化劑後,還要測定酸性中心的數目,酸性中心按強度的分布及其與催化活性的關系。進行這些研究的儀器設備,在國内基本上是空白,而在裡昂催化研究所一應俱全。在研究工作中,我可以随時送樣品去做相應的測試,有些儀器還可以親自操作。我的高真空實驗技術,包括玻璃配件的吹制都是在裡昂催化研究所裡學會的。我也從此進入了分子篩催化的研究領域,為以後的科研工作奠定了基礎。”
“機緣巧合的是,當時裡昂催化研究所有一位名為Michel Che的年輕人在C.Naccache的實驗室讀博士,他有中國血統。我們兩人在同一實驗室工作,辦公桌也是面對面,朝夕相處成為了好朋友。Michel Che的父親石光彥先生是山西忻州人,1918年與周恩來等同時赴法留學,後定居法國成為一名造紙工程師。他是一位愛國華僑,娶了法國太太,但一直沒有加入法國國籍。中法建交之後,他曾協助中國大使館在裡昂接待中國體育代表團和中國青年藝術團。石光彥從Michel那裡聽說有個中國人到了裡昂催化研究所,而且和他兒子在同一個實驗室工作,非常興奮。在我到達裡昂的第一個周末,他就親自到所裡邀請我去他家做客,給我介紹法國的風土人情,向我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的變化。在以後的交往中,他介紹我認識了将《紅樓夢》譯為法文的著名華裔文學家李治華先生和裡昂法中友好協會主席多林(L.Dorin)先生,使我在裡昂有了更多的朋友。”
“雖然法國人比較開放,但對第一個來自中國的人還是感到十分好奇。多數人對我的到來表示友好,并渴望從我這兒了解新中國的情況,還有人建議我找一部中國電影在研究所放映。我從大使館教育處借來帶有法文字幕的中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影片,于周末晚上在餐廳放映。許多法國同事帶了家屬和朋友來看這部電影,現場被擠得水洩不通。放映後人們議論紛紛,大多數同事反映很好,欣賞了新中國的文化與藝術。但有個别不友好的人到所長那裡去告狀。不久副所長B.Imelik找我談話,很嚴肅地問我‘你到研究所來是做什麼的?’我回答‘是來做研究工作的。’他又說‘那你為什麼在研究所進行宣傳活動?’我說‘所裡同事要求看一看中國影片,我找了一部中國的音樂與舞蹈的藝術影片給他們看,怎麼是宣傳活動呢?如果您有時間,可以請您看看這片子有無宣傳内容。’他說‘我沒時間看,盡管是藝術影片,希望你今後不要進行類似活動。’我把副所長的一席話告訴友好的同事,他們說‘不用理他,我們有欣賞藝術的自由。’”
“裡昂催化研究所的許多研究人員對我都非常熱情,使我很快融入了那裡的研究和生活,成為他們中間的一員。例如,J.Vedrine在所裡讀博士,他的夫人是所裡的醫生,他們倆常約我在研究所的餐廳共進午餐,在聊天中還常常糾正我法語口語中的錯誤,這對我提高法語水平 有很大的幫助。後來他還邀請我到他家做客,有時周末還住在他家的鄉間别墅。後來他一直是與我長期密切交往的好朋友。”
“另外,G. Martin, G.C. Gravelle, J.M. Basset等也常邀請我去聽他們介紹實驗室的研究工作,并将他們發表文章的單印本送給我。J.Vedrine專門研究催化氧化,G.Martin 研究雙金屬加氫裂化,G.C.Gravelle用量熱法研究化學吸附和多相催化,J.M.Basset研究金屬絡合物催化劑。D.Barthomeuf是國際著名的研究酸性催化劑的專家,當她知道我在研究分子篩時,就邀請我到她的實驗室參觀,并介紹她在矽酸鋁方面研究的方法、思路和研究結果,還向我具體講述了她的矽酸鋁催化劑酸性中心的結構概念。法國同事們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豐富了我在催化領域的知識,開闊了眼界,對我日後的教學和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并充實了我講授催化課程的内容。”
“法國人熱情好客,常會在周末邀請幾位好朋友到家裡做客,晚餐時談天說地,包括個人的趣事,一直持續到午夜以後。1966年的法國已經是每周工作5天,而且法國上半年的宗教節日很多,有過節‘搭橋’的制度。比如周四是節日,周五就被搭橋過去和周六周日連在一起休息四天。同樣,周二是節日,周一也被搭橋,這樣也有四天的假日。在這些假日裡,常有同事邀請我去家裡做客,還有人邀請我到他們的鄉間别墅,在那裡欣賞田野風光以及農民的畜牧和耕作方式。Wicker先生在阿爾卑斯山附近有别墅,複活節時,他特别邀請我去阿爾卑斯山教我滑雪。”

1967年4月再裡昂多林(Dorin)先生家中

在Alps山滑雪
“當時在Nacache的實驗室,我用順磁共振法研究離子交換後Y型分子篩的性能,經過一段時間的實驗,研究取得了很有意義的結果,導師Nacache要我趕快整理文章發表。但那時國内不允許向國外雜志投稿發表文章,認為這是争做資産階級精神貴族的拐杖。因此是否投稿要向大使館請示,結果教育處告知我不能與外國人共同署名發表文章。最終隻能由導師自己發論文,不能加我的名字。”
李宣文老師到法國裡昂催化研究所學習和研究,原定進修時間為三年,結果被“文化大革命”打斷,實際進修一年半後就不得不回國了。即使隻有一年多的時間,李老師也極大地開闊了眼界,學到了很多新的知識與科研技能,為回國後的科研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同時,李老師也結交了很多對中國友好、并願意無私幫助我們的國際友人,為中法友誼和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記者 | 郭九苓、肖熠、高珍、裴堅
錄音整理 | 郭九苓
文字編輯 | 郭九苓、李宣文
排版 | 祝晨旭